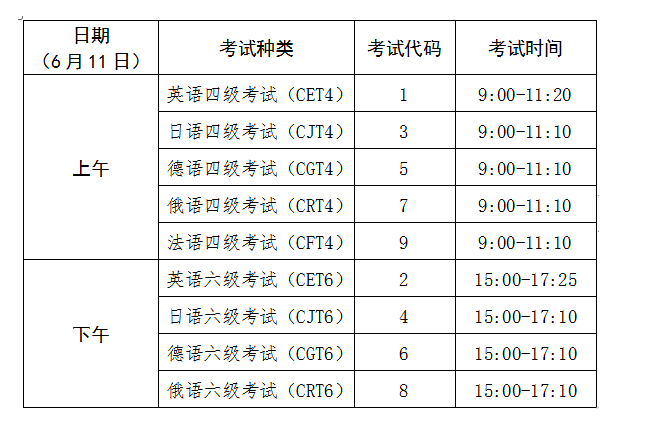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特点及防治对策 天天讯息
来源:人民法院报 2023-02-02 11:12:42
近年来,利用未成年人实施敲诈勒索、盗窃、贩毒、黑恶势力等犯罪的案件屡见报端,导致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更加凸显,既严重损害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也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应引起社会高度重视。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发展特点,我国相关法律和刑事政策均对未成年人作出了诸多特殊规定,以期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但一些违法犯罪分子却从中发现了可乘之机,利用未成年人自我保护能力弱、辨别能力低、易于控制指挥以及低龄未成年人无须承担刑事责任的特点,将未成年人充当“挡箭牌”或“替罪羊”,而自己则充当“幕后黑手”,由此导致陷入犯罪泥潭的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引发了诸多社会问题。如何针对当前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主要特点提出相应的防治对策,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一、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主要特点
被利用的未成年人往往是那些缺乏家庭或学校关爱的“问题少年”。重庆市南岸区和巴南区人民法院曾对1700多名未成年犯做过调查,调查显示大部分未成年犯缺乏家庭和学校的关心。对于成绩较差且性格敏感的未成年人而言,其往往缺乏与教师、家人的沟通,更易产生自暴自弃乃至逆反的心理,最终他们只有向社会倾诉心声。一些不法分子恰恰利用未成年人的这一心理,诱使他们加入犯罪集团甚至黑社会性质组织,让他们从学校中的“边缘化群体”演变为社会上的“边缘化少年”,最后成为“问题少年”和黑恶组织的成员。例如,长春的“血杀帮”专拉中学生入伙,专门寻找因学习成绩差、单亲等原因在学校和家庭中不被老师、家长关注的未成年人,利用他们内心敏感、容易自暴自弃的叛逆心理,有目的性、有选择性地拉拢初、高中生加入恶势力团伙,并针对在校学生实施抢劫、寻衅滋事、盗窃等违法犯罪行为。
利用的方式较为宽泛。在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中,犯罪分子的利用方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教唆、胁迫、拉拢、引诱、欺骗、招募、吸收、介绍、雇佣等。例如,有些犯罪分子以“提供工作岗位”为名,直接招募未成年人入伙,欺骗其实施犯罪。在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陆某运输毒品案”中,犯罪嫌疑人陆某等人便是采取出资的方式雇佣多名未成年人以体内藏毒的方式,多次绕开海关走私毒品海洛因入境,后再运输至四川、湖南等地。在广东省连州市人民法院审理的“‘犁庭4号’涉黑案”中,犯罪嫌疑人周某某则是通过网络平台拉拢、招募、吸收多名未成年人加入涉黑组织,通过收取“善后费”“保护费”等方式获取非法利益。
所利用实施的犯罪相对集中于侵犯财产类犯罪,其中敲诈勒索罪占比最多。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统计,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相对集中于侵财类案件,占比约为63%。其中,又以敲诈勒索罪数量最多,案件量接近侵财类案件的一半。此外,寻衅滋事、聚众斗殴等扰乱公共秩序类犯罪约占14%,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类犯罪约占14%,故意伤害、贩卖毒品、绑架等其他案件约占9%。
被利用的未成年人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的双重地位。从表面上看,被利用的未成年人直接实施了危害社会的行为,具有违法犯罪人的身份。但不容忽视的是,他们其实在更大程度上处于受害人的地位。正如美国犯罪学家詹姆斯·肖所言,参加团伙最终会导致未成年人的自我毁灭。团伙所涉及的对未成年人的信任,会导致一个危险和致命的游戏。团伙成员比非团伙成员更可能实施未成年人犯罪并变为犯罪的受害者。具体而言,首先,在犯罪团伙中,成年人往往起支配和管理作用,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成年人常常利用未成年人反抗能力较弱、易于控制等特点,直接殴打、胁迫未成年人,迫使其实施犯罪。其次,此类案件一旦案发,成年人为逃避处罚往往让未成年人投案顶罪。例如,在“靳白宇案”中,首要分子靳白宇为逃避法律责任,辩称团伙中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和他无关,自己概不知情,企图将寻衅滋事的罪名推给被利用的未成年人。最后,犯罪记录伴随被利用的未成年人一生,影响极其深远。尽管未成年人是被不法分子利用于实施犯罪,但其犯罪后形成的犯罪记录意味着社会对其作出了否定性评价。虽然该否定性评价是基于其过去的犯罪行为而作出,但是影响却是延续的,甚至伴随其终生。
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现象的防治对策与建议
将所有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并明确其所受刑罚的加重程度。尽管我国刑法中存在着一些对利用未成年人犯罪者从重处罚的规定,“两高两部”于2020年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严惩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的意见》中也规定对利用未成年人实施黑恶势力犯罪者从重处罚,但是这些从重处罚的规定较为模糊或狭窄,且并没有单独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规制条款,最终限制了对利用者从严、从重处理的效果。对此,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以及澳门地区的相关规定。台湾地区有相关规定:“成年人教唆、帮助或利用未满十八岁之人犯罪或与之共同实施犯罪者,依其所犯之罪,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澳门1997年《有组织犯罪法》第2条第4款规定,针对十八岁以下的人进行招募、引诱、宣传的,在五至十二年徒刑的基础上,要加重三分之一刑期。相较之下,关于利用者的刑事责任,上述规定有两点值得借鉴。一是将绝大多数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行为均纳入刑法规制范围。我国刑法总则中仅规定了教唆未成年人犯罪从重处罚的条款;刑法分则中也仅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等少数条款中实现了对利用者的从重处罚。因此,可以借鉴二者的规定,从行为方式上严密处罚利用者的刑事法网,最大限度地发挥“加重处罚”条款的效用。二是明确利用者所受刑罚的加重程度。我国刑法相关条款中仅原则性规定了“从重处罚”,但对于如何从重、从重的幅度,无论是刑法条文还是司法解释,均没有予以明确。因此,“加重二分之一”或“加重三分之一”的规定可以作为利用者刑罚处罚的参照,为量刑提供明确指引。
及时纠正未成年人涉财产犯罪的不良行为,加强对在校学生的管理。未成年人实施的财产犯罪往往衍生于平时的小偷小摸、强拿硬要等不良行为。未成年人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产生的不良行为得不到矫治是发生侵财犯罪的最大诱因。对此,在利用未成年人实施财产犯罪的防治上,需要父母、学校、社会机构在发现未成年人存在失范行为进而具备犯罪倾向时及时介入,鼓励未成年人通过从事合法的、有益社会的活动,对社会采取理性态度和生活观,从而形成非犯罪型的态度。基于这一时间分布规律,学校需特别加强对在校学生在夜晚时段的管理,及时发现学生是否有夜不归宿、盗窃同学财物等行为的发生。此外,社区、公安部门需在上述时间段加强巡逻和监控,提高监管力度;家长需及时了解孩子的行踪轨迹,对于有相关行为前科、经常夜出或夜不归宿的孩子需特别严加管教。
完善学校法治教育内容,采取多元化的法治教育方法,增强法治教育的针对性。首先,完善学校法治教育的内容。法治教育内容是提高法治教育效果的前提和基础,更是阻止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现象向校园渗透的关键。当前多数学校的法治教育往往无章可循,在内容上常陷入泛而不精的弊端。对此,学校的法治教育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法律理论和理念教育,涵括法律价值、法律功能、法律信仰、权利义务关系等内容;二是法律权利教育,涵括未成年人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参与权等内容;三是犯罪预防教育,旨在向未成年人讲解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犯罪成本、刑罚的惩罚性、不良行为的预防和矫治。其次,优化法治教育方式,增强法治教育的针对性。学校在授课方式上,应当采取学科渗透式的法治教育方法。既要开设独立的法治教育课程,向学生传授既定的法律知识,又要充分利用学科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的路径进行法治教育。对于独立的法治教育课程,可以通过模拟法庭等亲身参与的方式进行。对于学科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的课程,各科教师在自己的科目中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展法治教育。例如,地理老师可以结合地理环境的特点,讲解自然环境与犯罪的关系。
基于未成年人的受害人地位,建立被利用于实施轻罪的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发展,对未成年犯复学、升学、就业以及顺利回归社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在目前的条件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尚无法真正达到消灭未成年人犯罪前科的效果。例如,《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第64条和第65条分别规定了具体的查询和解除封存条件,一旦上述条件得到满足,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就将“重见天日”。事实上,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进行消灭业已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例如,日本1948年少年法第60条第1款规定:“少年犯罪执行完毕或免予执行,适用有关人格之法律规定时,在将来视为未受过刑罚处罚。”另外,《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第19条也规定:“释放时,少年的记录应封存,并在适当时候加以销毁。”就我国而言,自2003年以来,河北、山东、上海、江苏、贵州等地便已纷纷采取颁发前科消灭证书等诸多措施积极探索和尝试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然而,受前科消灭制度在我国整体上发展不利的拖累,我国至今未建立起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近年来,受醉驾、高空抛物等轻罪入刑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建立与高发型轻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前科消灭制度完全可以从率先建立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来积累经验。鉴于被利用于实施犯罪的未成年人兼具施害人和受害人的双重地位,其犯罪往往呈现出冲动性和盲从性,与预谋性、组织性、长期性的成年人犯罪相比,主观恶性微乎其微。因此,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规定的基础上,针对被利用于实施轻罪的未成年人构建前科消灭制度,不仅不会弱化对社会的保护,反而有利于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可以为我国建立完善的前科消灭制度提供宝贵经验。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 李振林)